废话一通先
“你相信中医吗?”这是“头条”布置下来的一个思考题。因这段时间忙于完成我所在市教育局布置下来的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之一——“公需课”的作业,而未能及时来写“头条”的这个作业。这里头有原因:教育局的作业不完成或没及时完成,那么它本想补助给你的那笔每年一两个嗒不溜的津贴就有了理由不发放给你,那么,看在大洋的份上,我得甩开火腿以辫子不沾背的速度跑去完成了它先;但“头条”这边,作业完不完得成,反正都没津贴一说,所以我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可以早写,也可以晚写,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废话说完了,我再来写正文,这种笔法,不是春秋笔法,是忽先生笔法,这里借用一下。
正文
你相信中医吗?这个问题问得就有问题:回答相信,错的;回答不信,也错的。甚至连忽先生“你相信上帝吗?”那样的回答,我认为,也是草率的,而且带有严重误导性。这在逻辑上叫做故意让人陷入两难困境。然而这岂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为此,我得讨点巧,绕着弯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争取做到首先不落入你下的套、挖的坑,然后还能尽我所能地来组织成一篇作文儿,从而完成一份答卷的上交。
对中医的态度,我大抵经历了一个从相信,到迷信,到不信,再到后来的冷静想想,觉得还是可以信它一信,但未必全信的过程。
这里,我得以我亡妻的逝为分水岭。
分水岭的那边,我对中医一直是信的,后来发展至于迷信。
打从记事起,我的母亲就教给我一些最基本、最朴拙的中医知识,比如折耳根、地丁、桑叶、桑葚、猪屁股(不是猪的屁股,是我家乡的一种草药,学名我叫不出)等等等等草药的常识性药效:大概都可以归结为“清热”“散寒”四个字。我的母亲,斗大的字,也认不识一箩筐,所以能说出这些草药的能“清热”“散寒”来,已属难能可贵,或干脆说是到了她老人家脑袋里所能装的中医药学识之极限,也错不到哪里去。
话说到这里,不妨拣一个我孩提时代的至今依然让我毛骨悚然的故事,来讲讲给大家听。
初冬的一天,放晚学时分,我书包刚一丢,作业都还没写,母亲就下诏:去“敲”折耳根。是的,初冬时节,正是折耳根喷薄分娩出头来的大好辰光。这时去敲它,那个嫩啊,各位,还用我取譬么?不过,这里有必要按一下:我们川南一带的方言,是颇有些意思的,都说“敲”折耳根,不说“挖”折耳根,虽然在实际操作上,它就是挖折耳根,但我们那里偏不说挖,非得说敲,很有意思吧?更不能说“割”折耳根,因为折耳根的根根是尤其精华的部分,割,你是割不起来它的根根的,非得“敲”不行。后来我考取了中文系,再后来又走上了语文教师的讲台,这才约略醒悟:所谓的“敲折耳根”者,大概应该是“撬折耳根”的谐音也。
回到故事来。于是,奉母亲大人懿旨,我拿了镰刀,背了小背篓,——就这两样行头,是不是就已颇有了几分湘西妹子儿的“原生态”,换言之,是不是有点儿青涩、甜美,还略带一点“辣妹子儿辣辣妹子儿辣辣妹子儿辣妹子儿辣辣辣”的感觉呢?——就去敲折耳根。
折耳根的生长习性,因敲它得太多了,我是知道一些的。它们大抵爱长在田埂(我们那里习说“田坎”,以下就说“田坎”了哈)的壁上,尤其是一些水田的田壁,因水分充足,若还能少被或不被人“敲扰”,则往往一丛一丛地长在那里,长得那才叫一个自在坦荡、茂盛兴旺,那情形,实在惹人要为之狂奔过去——狠狠敲它一敲。
这不?我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去处:一块清澈见底,水草、鱼虾,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蚂蝗,一应清晰可见的水田,四围则是田坎。不必说,这田壁上一定长满了折耳根,而且是长得相当哇塞(趁着现在还比较流行“相当哇塞”,得赶紧多用用)的折耳根,这才能把我这娇嫩可人的小屁孩给吸引过去,并为之毅然不顾水田的刺骨之寒,人家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我是挽起裤腿就往田头冲。
这一冲没什么,你冲下去以后,不多一会儿就赶紧上来呀,娃,那才不至于冷得嘴唇发乌,更不至于两腿都爬满了那令人头皮发麻的蚂蝗呀,我的个小四川呢!可你为啥偏偏冲下去就只顾泡在那一处原地不动呢?原地不动蚂蝗不爬死你才怪。
这能怪我吗?我之所以泡在那里原地不动,不就是因为那里的折耳根长得实在太好了吗?敲都敲不完。
好,好好好,依你,长得好,长得好,长得好你也不能只顾敲那一处啊,换着敲呀,正所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完全可以来它个东敲一镰西敲一刀噻;有蚂蝗的水田里头,大人们都晓得,要不停挪动步伐,才不至于被蚂蝗爬呀。
可我怎么晓得这个道理呢?我是小娃儿哒。
那我问你:后来你是怎么晓得你满腿都爬满了蚂蝗的呢?
哦,我是在小背篓装得已再也装不下去折耳根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爬上田坎来的,爬上田坎来了以后,正准备洗脚杆呢,这才晓得的。哎哟哟~~~,哎哟哟~~~,你才不晓得哟,兄弟,那可是满腿都爬满了蚂蝗啊,密密匝匝,密密匝匝的,哎哟~~~啧啧啧,快把眼睛给我蒙上,我不敢看了又!
但不看不行啊,你必须收拾它才行啊。
哦对,是必须看,再恶心再肉麻再恐怖,都得看,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啊。然而,看到那满腿的蚂蝗,啧啧啧……顿时就吓得小小的我相当“哇”(不是相当“哇塞”)的一声,就嚎啕了起来!
你娃真是够啰嗦的。快别啰嗦,别嚎啕了,赶紧告诉我,你是咋收拾那些个蚂蝗小儿的,最后?
还能咋收拾呢?我就拿镰刀去刮他们呗。可哪里刮得下来呢?一条条蚂蝗,密密麻麻死死贴在我白白嫩嫩的脚杆上,怎么刮也刮不下来,非但刮不下蚂蝗来,反倒深深地,深深地,因情急而深深地,刮进了我白白嫩嫩的肉里去了,一时间,鲜血那个直流啊,流啊,流啊…………小小年纪的我,就为了吃那一背篓的折耳根,就为了清点热,散点寒,殊不知,却被蚂蝗欺负得恁个惨!哎——,往事不堪回首哦,每每回想起那一幕,我就痛!
别感叹先,还没完,你必须告诉我,后来那满腿的蚂蝗是怎么没了的呢?
我也不晓得呀,反正一是满腿的蚂蝗,二是鲜血直流的伤口,此情此景,跟好莱坞“肉麻片”中那些恶心死了的镜头有啥上下左右呢?这让一介小屁孩的我,实在无招可支,情急之下,我只好背起装满了折耳根的小背篓飞叉叉往家跑,回家去找妈妈。不是找妈妈算账——不该命令我去敲折耳根,而是找妈妈给我支招——拿下蚂蝗与伤口。可不知为什么,嘿~~~等我跑回家的时候,腿上的蚂蝗竟一条也没有了,不知何故。但那伤口,那镰刀割下的伤口,虽则是被妈妈用从我家老墙上抠下的几块“蜘蛛窝”来贴起了,血也因此被止住了,但至今,那伤口仍在我心里,淌着鲜红的血。
不啰嗦是已经啰嗦半天了,不多下面这几句:我疑心妈妈那时的用老墙上的“蜘蛛窝”来给我贴伤口的做法,也应该归于“中医”,这大概等同于现在的用“创可贴”,效果还蛮好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有看官大概会批我了吧,说我跑题跑哪去了哟,不是在谈相不相信中医的问题么,咋一跑跑到家乡的田坎上去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来思考的,故事中的我,不就是在相信“中医”么?折耳根清热散寒嘛,凉拌来吃也好,熬水喝也好,都是极好的食材与药材,所以要去敲,不然,我哪会付出恁大的牺牲呢?窥折耳根这一斑,即可见中医之全豹。在此意义上,应不算跑题。只是详略的拿捏,未必合式,这倒是我该多加考量的。梭蕊。
跟放电影一样,到这里,镜头打出了“2014 夏”的字样。
是年4月29号,已故的拙荆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的建议,回家“保守治疗”。大家都懂,所谓“保守治疗”,就是“无需治疗”。
但我不甘心。亡妻更不甘心,她曾对我说,哪怕把房子卖了,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把这该死的病治好。她还说过一句话,至今清晰犹在我耳畔:“这世界,太美了!……”那一刻,她跟我一起,坐在从门诊回家的的士车上,车窗外现代、繁华而美丽的市容市貌,飞也似地往后奔去。
于是我下定决心,哪怕用尽一切办法,都要为伊疗治,以挽救她实在是太“英年”的生命,并让伊在这“太美了”的世界里,能尽可能多地体味一些美的滋味。
那么,既然L市的最大最好的医院都说“保守治疗”了,那么L市的其它医院,也就无需去求告了。我便带着病痛中的妻子,辗转去了C市第三军医大,结论照样很清楚,明明白白地一点不给人希望,还是:回家保守治疗。
于是,西医的形象在我心中瞬间崩塌,幻灭:面对癌症,尤其是中晚期癌症,它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有亲友就建议,可以采用中医治疗,大约可以有一些“延缓”之效。延缓?要的不就是延缓么?谁活着不是为了“延缓”呢?于是多方打听可以“起死回生”的“妙手”。从L市各大有名的中医院,再到稍微次一些的中医诊所,最后连所谓的能“拿手”该方面病症的“偏方”医生,我都一一寻访遍了,其结果,充其量是聊胜于无,而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对病中人和病外人的一点安慰而已。妻子的肚子照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腹水的不断产生而一天天大起来,其速度之快,估计比孕妇肚子之长还快十倍都不止,真够怪吓人的。
我在日复一日的惶恐中,忘记了是从哪里突然得来了一消息,说贵州的凯里有个苗医,专治肝癌,十拿九稳。于是我不顾一切,连夜连晚,八百里加急赶往凯里,找到了那个苗医。于是将妻子的病情描述给他,又于是以昂贵于一般中医十多倍的价钱提了大大的一袋子药(一次开20天的药,里面有20袋分开装满草药的小纸袋)回来:以为这便是提了让拙荆重生的希望回来。
这苗医着实与其他中医大有迥异,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四点:一是要用到他们凯里土生土长的一种我叫不出名来的乔木的树皮,以及一种动物身上的某个器官,但到底是何种动物,外人一概不知,绝密,那我们咋知道有这回事儿呢,是他讲给我们听的,但不许我们看,也不让我们知道动物名,相当神秘;二是按他的吹嘘,已有很多高级别官员求他看过病,拿过药了,有照片为证;三是每天必须用到新鲜桐叶,用法是将其捣碎,再外敷到病人的肝部所在的肚皮上;四是据说这苗医深居简出,很多时候,病人(说“顾客”更为准确)连见其真佛一面都难,(我前后去过两次,运气还算不错,两次都见到真佛了)多数时候,都是他的几个儿子和徒弟们料理诊所,捣药的,切药的,收款的,抓药的,各就各位,煞有介事。有人会问,这中医不给病人切脉吗?答:来者都是肝癌患者,不用切脉,方子都是一个。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让这苗医的诊所天天门庭若市,更重要的一点是,连我这样的“知识混子”,也油然生出膜拜之情来,并将妻的重生的希望整个地托付给他,一切听命于他,他说啥就是啥,一概不折不扣地执行:包括价钱和药方的煎熬与服用之法等。
到最后(拙荆去世前不久),我还“租用”了专车,专程从我的家乡四川的L市驱车前往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凯里,去恭迎这位“妙手”亲临我寒舍为吾妻“望闻问切”。这一次,老实说,我花的重金可真是不轻,不多谈了。
这便是我迷信中医的阶段。
然而,拙荆还是于是年6月30日晨,溘然长逝。从4月29日确诊,到6月30日去逝,说刚好两个月,在文学上,是讲得通的。而这两月间,确然让我看到了西医的无能,更看到了中医的不仅无能,而且虚伪——不能偏说自己能。
自此以后,我翻越到分水岭的这边。
而分水岭的这边,就简单了:我开始彻底不相信中医了。这理由还用我多说么?再者说了,连我们的鲁迅先生不也曾经恨死了中医么?就因为他所遇中医一个个是庸医,医死了他的父亲。
如今,事易时移,情随事迁,我从感情的冲动中多少算是走了一些出来,委实变得冷静——也变得“冷”——了许多。
所以,当拿到“你相信中医吗?”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思绪万千,且杂乱无章。
但落脚之处,还是归于了“冷静”。于是,我想到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也想到了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这些神一般的中医人物,另据《红楼梦》所载与学者的考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曹雪芹也是一位中医高手,并常藉此治病救人。那么,我之所以要联想到这些典籍和这些中医名家,其目的就在于要说明一点:中医是有它的道理的,想来,如果说在西医引进之前,我们的炎黄子孙大概一代代都只能靠中医来治病,这话应该十有九靠得住;所以一棒子打下去,想置中医于死地,不是你脑壳发了昏,就是你偏见太甚。
所以,我看可以这样来切分一下这个问题,所谓中医,实际上含着两部分意思:一是中医之道,二是行中医之人。那么回到本次题目——你相信中医吗?我猜它大概是想问:“你相信现在的行中医之人吗?”那么,明白了这一点,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一言以蔽:中医之道,一定有其灼人的光芒,这部分要信;而行中医之人,却一定有不在少数的庸医甚至骗子,这部分信不得。
那么我今天的作业,写到这里就应该说欧了。完了还没事找事,也出个题目玩玩,大家拿下去思考:你相信西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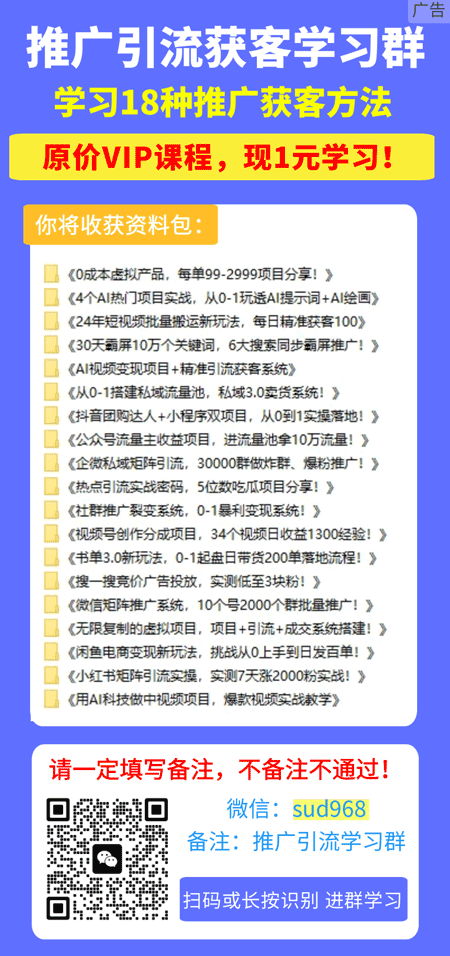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dasum.com/8037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