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谁都没想到失踪十几年的她会突然回来,家里人和亲戚都猜她要么死了,要么被骗到山沟里给人当媳妇去了,有的联想丰富,说有可能被拴着铁链,吃的狗食,精神失常……
有一次跟我妈聊天时,她发了一张照片,问认识这个人不。
我把照片下载下来,仔细端详,放大缩小,前后倒置,左右翻转。
我慢悠悠地说:不会是美迪吧!
我妈哈哈大笑:嗯,猜对了!
我像郭德纲那样一只手捂住嘴巴惊道:天呐!她还活着!
“咋说话呢,人家活的好好的,而且开的车很气派,是四个环……”
荣归故里啊!我的天啊!她爸妈快高兴疯了吧!
我妈后来说,美迪回来,大家都有点不认识了,不但着装时髦,关键还整了容,眼睛开角,下巴打了玻尿酸,双颊削骨,俨然一个快手和抖音中的网红女。
美迪和我是同村的中学同学,本人个头不高,只能说长相清秀,归不到美女一类。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3月份,她找我借钱上网,我没借。
高考开始倒计时,我规劝她赶紧好好学习,不要沉迷于网络,她说:不借钱拉倒,废话真多,亏我拿你当朋友……
就是这次,她不见了。
自此一别近十年。
起初,我听到她失踪还是我妈问我:她父母好久没联系到女儿了,你和她一个学校,有没有见到。
我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找她班主任打听,老师和家长的说法一样:已经失联十天,宿舍东西都在,问了其它同学,都摇头说不知道。
她平时只顾上网,和同学朋友不善交流,所以失踪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报警后,警察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出了这事以后,我开始有点后悔没给她借钱,或许她真遇到什么难处。
高三是高中生最特殊的差别对待,对高考有希望的学生加紧扶持,力争榜上有名,对于无望的学生放任自流,自生自灭。
美迪属于后一种,她失踪后,家里到学校讨要说法,学校对于这件事冷处理,因为美迪上网成瘾逃课频繁,很早就通知过家长。
母亲整日哭哭啼啼,父亲以做生意为由,天南海北找女儿。
一个如花似玉的丫头生死不明,后来大家都猜测她跟网友见面,或许被拐卖到大山里去给人家当媳妇生娃,因为这样的事网上也没少报道,而且搜救的难度系数大。
我们村里就有两个女孩在外地打工被人骗了去。
一个还在大院锁着的时候就已经逃脱了。
另外一个女孩被拐卖到河北一个小山村,前几年回来时候已经带着两个娃,看了一眼父母,带着孩子又回河北老家了。
NO.2
美迪这次回来像是中了状元的驸马爷,一路敲锣打鼓回家省亲;在当地高档饭店大摆宴席,请邻居亲戚好友好吃好喝,大家一时感慨万千,有的人猜测她是当小姐了,有的人猜测给富贵人家当二奶了,甚至还有的人猜测去泰国贩卖玉石发大财了……
社会一向很奇怪,哪有什么正义感,吃着人家的饭,还说着不好听的话。
她回复大家的说辞是:当年离家出走,是南下广州,她忍着多年不联系,是想混出个人样来,如今做的是水产生意,一切越来越好,感恩大家多年牵挂……
她在省会城市给父母买了一套房,靠近湖边,因为我们这边缺水,稍微带点水系,都会被开发商夸张成三面环水,玉带环腰,贵府重地。
因着我在本市有些时日,她便找我给她推荐房子,她强调一定要物业好,环境好,适合养老。
我介绍完房子之后,她又要谢我请客吃饭,我说都是老同学举手之劳,她说见面聊聊,我对聊聊有着本能的兴趣。
我们是在一家私密性挺好的餐厅就餐,她一席烟灰色落地长裙,身姿窈窕,锁骨很美,若盛满水能养鱼,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冷艳。
十年没见,我们只是笑,连善意的恭维话也说不出口。
但是她的变化的确令我很惊讶,整容的幅度很大,额头很饱满,双颊削骨后,下颚深陷,显得下巴很尖,眼角开的有点大,眼睛里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不知道是不是整过容的原因,我们之间有一种陌生感。桌子上的菜看起来很诱人,我总是放不开嘴吃。
“酥骨鱼没有广东的好吃。”
“听说你们广东菜挺丰富的,有整盘蛇,有猴头,穿山甲……”
“现在整治的厉害,很多稀有品种,饭店都不会有,但有些人照样能吃到。”
她不吃了,放下筷子说:在你看不见的角落上演着各种无耻恶心的戏码,她有点怔然,或许是想到了刚好能印证这句话的事儿。
我点头称是,因为我常年不出门,对于闯荡江湖的人,有着天然的仰慕。
其实我在等她的下文,她需要一个出口来证明自己这份来路不明的财产的合法性,她想通过我来作为传递的媒介。
耶稣30岁在人间传道的时候,成名不是在家乡,而是其他地方。等他回到家乡,并没有人信他,而是对他指指点点,看,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跟我们一起洗衣服的玛利亚吗!他的弟弟妹妹,我们不是也一起玩耍吗!所以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而我正需要这样的素材,所以洗耳恭听。
在这里我只讲重点,而且很多细节她不愿意多讲,我也不愿意揭开当事人的伤疤,文下多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
NO.3
我2003年失踪,当初你不给我借钱,我问别人借了50,这次回来给人家买了一件价值2万的貂皮大衣。
看来她还挺记仇,我嘿嘿一笑,算是掩护我自己的自尊心。
她说的云淡风轻,我听得沉重万分。
我说要是知道有这样高的回报率,当时就算卖血卖肾我也给你凑个万儿八千,你是不是回来给我买一套房。
她说差不多。
我在2003年4月份,下午六点钟,刚好是周一下午,逃课了,和网友在地宫广场见面,对方是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头发黑亮,穿着黑色的夹克和黑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黑色给人一种神秘感,小女孩都喜欢神秘。
男人说自己在南京工作,到西安出差,离这边不远,过来看看我,劝我不要经常熬夜,更要以学业为重,他会等我,他的表白很动情,可以说,丝丝入扣。
想一想,这样成熟的男人对着一个小女孩表白,我怎能不雀跃,当时心里满满当当都是感动和快乐,他嘴角噙着那抹笑,后来回想,那是大灰狼从小红帽那里得知外婆家后得逞猖狂的笑。
我们之前网聊了三个月,虚拟的世界里对我嘘寒问暖,再见真人,虽然有点忐忑,总体上很有好感。
小女孩对于事业有成的中年大叔有崇拜、依赖、爱恋,甚至有奉献的情怀在里边。
我们俩一起吃过晚饭,我要回学校,他说包夜上网,那时候高中生包夜上网是常事,不像现在电脑这么普及,因为包夜比较便宜。
好像那男的有一股魔力牵引着我,我紧随其后,他说话处处征询我的意见,而不会强制我,尤其看我的时候,眼神温柔极了,我放下防备。
在包夜中途,他又提出回家休息,说不放心留我一人在网吧,回学校也是关门,不如去他那将就一下,或者在宾馆给我重新开一间房,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你看男人的套路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可是上当的小女孩依然甘之若饴。
他带着我坐上出租车,直接到汽车站附近的酒店,刚一进门,男人的本性暴露,他急不可耐,对我上下其手,当时我害怕极了,对他又撕又打,我一个小姑娘压根无法反抗,他说:你再叫,现在就杀了你。
(小姑娘们要是遇到男人想要强暴你,如果在封闭的空间,尽量不要喊叫,保命要紧,伺机逃跑,随后举报,因为喊叫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很有可能使得对方在恐惧暴怒之下做出杀人越货的举动。)
他当时面目狰狞,太阳穴暴出青筋,从眼角延伸至面颊。
恐惧、愤怒使得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任其摆布。当时我没想那么远,或许他只是单纯地想睡我,而不是谈虎色变的贩卖人口。
第二天他开始洗脑,甜言蜜语就是糖衣炮弹,尤其早晨男人说爱你,无非就是子弹上膛,再打一发。
我被吃干抹净后,他还是不放我回去,甚至说已经是他的人了,要带我回老家。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到害怕,这要是一走,肯定再难回来,于是我跪下来求他,说我爸妈没有女儿会疯掉的,保证把昨晚的事不说出去,也不报警,我甚至寻死,一头撞到床头,没有流血,只是一个大包,对方不吭声,只是坐在床边用床单擦他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
下午三点左右,他堂而皇之地牵着我的手,离开宾馆,到了长途汽车站。
他的另一只手里攥着那把小刀,只要我稍微用力扯一下,他便会使劲拉我到他怀里,用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再乱动,就宰了你。
这时我问当事人:当时你为什么在路上不大声叫啊,尤其在汽车站,有巡警,肯定能活命。
她双眼无神,把夹起的菜又放到碟子里,愤恨地说:对方说如果我喊叫,就会杀了我全家,因为在网聊的时候,我脑子抽风,竟然把自己的家庭住址都告诉了对方……
NO.4
坐汽车三天三夜,到的地方不是南京,而是贵州某一个不知名的小县。
(坐汽车不需要身份证,坐火车需要,而且火车站人多口杂,容易露馅)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女人(她说老女人的时候,牙齿都在打颤),他们对话是地方方言,说说笑笑,叽里呱啦,我连一句都没听懂,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他把我交给了那个女人,我起初以为是他的母亲,后来才得知根本不是,而是小头目,就像现在直销,他们之间也有链条,层层分级,这种拐骗人口的买卖不会经手很多人,容易暴露。
这个男人在外围撒网,专门拐诱小姑娘,得手后,为了安全起见,会亲自送到二道贩,再由二道贩根据“需求”分发各地,而我算是年龄大的,也是上过学的,害怕途中出现意外,留到当地了。
她们都称她花婶,花婶带着我坐上一辆面包车,还有两个粗壮的男人,坐在我们身后,眼睛像狼一样泛着幽光,除了司机前面的车窗玻璃可以看到路,其它玻璃全贴着东西,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我当时就像一头蒙着眼睛布拉磨的驴,任其摆布……
兜兜转转,来到一个院子里,屋子都是用柱子支起来的简易草屋,没有窗户,门是木板门,有一把很大的铁锈锁,院子里有四个小木屋,柱子之间用绳子缠着,绳子每隔一段距离会有一个小铃铛,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只要谁进进出出都能听到铃铛响。
我被带到其中一个小屋子里,里面关了三个丫头,我最大,十七岁,有一个十三岁,一个六岁,都比我来的早,她们头发乱蓬蓬的,好像有点不对劲,不说话,不哭闹,眼神呆滞,只是定定坐着。
我们在一起只待了一天,只问到了年龄,我跟她们讲话,而这两个小姑娘戒备地看着我,再也不说话。
这个屋子差不多三四十个平米,里面放了一张大木床,拐角处放着一张小桌子,再无其它,头顶有一个小灯泡,却不知开关在哪里?
天黑了很长时间,花婶给我们端来饭菜,我只尝到野生蘑菇的味道,其它菜尝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后来我再也没吃过蘑菇……
花婶进屋前开了灯,才知道开关在外面。
我因为坐车,很累,和着衣服在那个木床上躺下睡着了。
那晚又恰逢下弦月,要等夜里十一点钟才会升起来,因而夜色显得更浓。
半夜醒来,不知道几点,隐约看到那两个丫头一直坐在地上,我也没有了睡意,开始想着如何逃脱。
门缝里射进一道光,很暗,只是比墙壁和地板颜色亮点。现在我有的是大把时间后悔,如果没有来到这里,或许还坐在亮堂的教室里。时光毕竟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人的四周只剩下时间,就会幻想,幻想过去、未来,唯独不想现在。
或许我年龄大,知道哭闹没有用,花婶总是对我笑,也会说一些话,虽然听不懂。
第二天,那两个丫头被花婶带出去,再也没看到,在拉扯的时候,我看到她们脖颈,手腕上面布满了红印青痕。
我心里很恐慌,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终极目的地在哪?
当天下午两个男一女来看我,他们穿的很寒碜,其中有一个男的腿有点跛,不知道他们和花婶说了什么,我就被带走了。
弯弯绕绕的羊肠小道,昏暗的天空,阴沉的没有一点色彩。他们一前一后,我走在中间,已经习惯了被当作重点保护对象的待遇,我反而没那么恐慌了。
路上遇到村子里的人,我明显能感到他们对我的打量还有满意的笑容。
连绵起伏的大山,一个接一个的陡坡,还有两边郁郁葱葱的树木,如果不是被贩卖,其实那的空气也还好。
不错,我就是被卖到了这家,至于多少钱,我还真想知道。
而那个跛子,就是我的男人,他不仅跛,还是个聋子,他也不是全聋,大声喊话,他也能听到。听说小时候高烧不退,打错针了,没有及时医治,落下了耳疾。他还有三个弟弟,再加上家里穷,到现在娶不到老婆。
当晚,他们把我和他安置到一个小角屋里,里面放着一个掉了漆的大红木箱子,一床又脏又烂的棉被,一股霉味,让人很恶心。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表情,当天晚上,他高兴的直搓手,对着我笑,还拉我,我甩开他的手,他也不生气。我后背紧贴着墙面,一脸戒备地看着他,你也知道,我能扛多久呢。
他的力气很大,嘴里有一股恶臭味,压在我身上,像一个畜生来回晃动,我想杀了他,他把我折腾的一点气力都无,你不懂,和一个畜生干那样的事,比死还难受……
起初感觉每天都要挂,人的适应能力超强,那样猪狗不如的日子,我也撑下去了。
第二天,他们把我锁在家里,一家人出门干活,门口拴着一只大狼狗。
吃饭的时候,给我端到小黑屋里,我一个人吃,有时他也陪我,他们家人好像很少说话,总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逃跑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在脑子里盘旋,只有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才会装出一副痴傻呆萌。
这样的日子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我知道很多被贩卖到外地的女孩各种抗拒,其实抵抗根本没用,反而会消耗你的精力和智力,伺机逃跑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这里太穷了,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食物也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汤。
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
而这里大多都是干人,年轻力壮的大都出去打工,剩下老弱病残苟延残喘,他的三个弟弟都外出打工了,基本没见过面。
孩子大多数为留守儿童,脏烂,可怜、因为各种原因惨死成为常态,就像一棵棵胡乱生长的野草。
对了,我害怕怀上他的孩子,每次我们做完,我都会找借口蹲在地上使劲晃,就想把那些肮脏的液体倒出来,我不能怀孕,尤其他的种,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
好像我的身体不容易怀孕,那么多年,总有漏网之鱼吧。
因为我长期没有怀孕,他们对我态度愈加冷淡,不再终日锁着我,反而带上我出门干活,干活的时候我就研究地形,还是那些大山,看不到尽头,我心里哇凉哇凉的。
有时候我望着望着,就失神,那个男人会在我的脚后跟上一锄头,那个聋子经常打我,好让我乖乖听话,他是我这世上最讨厌的人,没有之一。
我问她:你有没有给人家生过孩子。
她慢腾腾地说:我不容易怀孕,后来还是生过一个,病死了……
NO.6
那儿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狗。
他们家算是在这个村子中间,还在低洼,山坡处也有人家,逃起来很难。
我不能半夜跑,这里的狗凶猛高大,要是被逮住,吃的连渣都不剩。
如果失败一次,终身也别再有这样的念头了。我等待机会正大光明走出去,这机会一等就是六年。
他们这边人干活有个特点,早晨九点出去,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回来吃饭休息,然后下午就在门前干点零碎小活。
有一天,下午两点多,我那个婆婆突然抽搐不止,因为生炉火做饭一氧化碳中毒,昏迷不醒,口吐白沫,公公常年干活两条腿都成O型已经跑不动了,而那个男人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公公让我去找他回家请医生。
我血脉喷张,终于有机会让我一个人出去,我在那条小土路上,边跑边叫:阿婆快死了,快来人啊,阿婆快死了,快来人啊……
就这样,喊了一路,嗓子撕扯般的疼,后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张大嘴,笑着,哭着,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不能哭,一哭跑起来肯定慢。
我跑了三个小时,终于看到一辆拖拉机,我搭了一程,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要能到大一点的镇子或者县里,就好办多了。
逃离的村庄和孤单前进的我,两边都闯入黑夜。
现在晚上做梦,我还能清晰地梦见:遥远的天边,一个破布烂衫的疯女人跪在那里笑得前仰后颠。
她说着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紧紧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别怕别怕,你已经回来了,别哭别怕。
NO.7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个世界变化太大太快了。
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被欺骗,在我逃出来后,觉得没有什么能打倒我,即使后来遇到多大的坎,我都能笑着应对。
她说也不敢向别人说她就是被拐卖的女孩,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会同情你还是嘲笑你。
她说想要唱歌,让我点歌,她点酒,我唱了《精忠报国》和《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主题曲之后,她抢过话筒,唱了粤语版的《大地》和《红色高跟鞋》。
……
后来,我俩都有点累,她说着说着便会沉默,抽烟喝酒,半天才聊一句,还走神。
她说:现在虽然生意有点起色,再也不会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就是忽然觉得辛酸,竟没有什么欣喜之情。
临走前她又跳上桌子,提起裙子,举起酒瓶,咕噜咕噜大喝几口,醉眼迷离,问我:你觉得我走这一场,划得来吗?
我既羡慕人家现在的气场,又伤怀她惨痛的过往,举起酒杯遥遥恭祝她余生不再受这样的罪:世上没有永远的事,一顿饱餐也不过只能维持三两个小时,生命不过数十年的事。不要钻牛角尖,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她酒后略显狂态:没有人爱我也不要紧,我爱自己,仗已经打完了,我将慢慢收复失地……
像美迪这样死里逃生,又触底反弹的实在太少,由于字数太多,待我下次详解她在逃出来后又是怎样的江湖刀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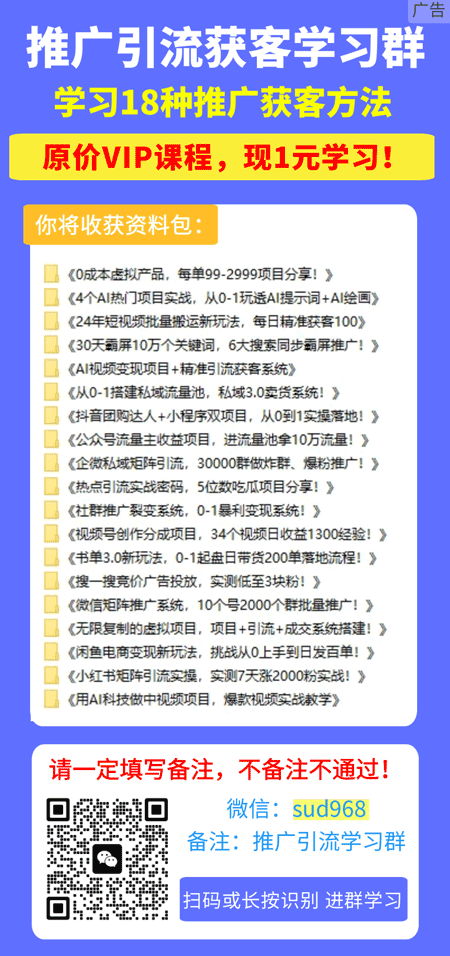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dasum.com/43060.html
